写在本系列前面
- 作者不懂philosophy,如果你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去反驳我,那么你就是对的。
- 本系列无限期拖更,因为我很懒。
- 如无特别标注,所有的引文均引自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版第二版)》[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 王庆节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
- 关于原文的解释,基本源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存在与时间>释义》张汝伦 著
- 如无特别标注,专业词汇的翻译以上面所说的《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版第二版)》中的翻译为准。
正文
听作为人的官能之一,倒是再常见不过的一种现象了。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的听,总是固有而并非主动的,即只要我们是醒着的而并非听力受损的,我们便不得不听。但我们又常有“耳边风”、“对牛弹琴”之类的说法来形容一个人“没听进去”,似乎听又是一种可以主动为之的行为——事实上“耳边风”这个词算是巧妙,它同时展现出了那个存在论上的听和生理上的听。
那个在责备别人“没听进去”中应该是的“听进去”的状态中的“听”,大致便是那个生存论上的听,那是一个建基于领会(Verstand)上的听。这个领会作为此在(Dasein)在之中的生存论建构的一环,显然也是存在论上的领会。
世界的在此乃是“在之中”。同样的情况,这个“在之中”也在“此”,作为此在为其故而在的东西在“此”。在“为其故”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本身是展开了的,而其展开状态曾被称为“领会”。
——第三十一节
要是一言蔽之,无非是在说此在是领会着存在的此在,包括在世存在的生存结构,当然也包括了领会本身。关于存在之领会内容诸多,在此暂不一一展示。
领会的筹划活动本身具有使自身成形的可能性。我们把领会使自身成形的活动成为解释(Auslegen)。领会在解释中有所领会地占有它所领会的东西。
——第三十二节
我认为这个“成形”是比较形象地讲法了,我将之理解为领会通过解释来“具体化”,若要用主体论一点的说法,就是让在我“观念”之中的存在理解通过实践活动“体现”出来。但不是说出来,而是以一种“作为……”结构将其展开。这要与前面讲的世内存在者的展开的内容联系在一起。
寻视(Umsicht)依其“为了作……之用”而加以分解的东西,即明确得到领会的东西,其本身具有“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这样一个寻视上的结构。寻视寻问:这个特定的上手事物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寻视着加以解释的回答是:它是为了作某某东西之用的。列举“为了作什么”并不单纯是给某某东西命名:问题的东西被认作为某种东西;被命名的东西也就作为那种东西得到领会。
——第三十二节
这里的回答显然不是在说那个具体的答案,而应该是在操劳的对工具的使用之中的回答,是你在问别人“这个锤子怎么用”之际,别人说“你看好,我这就示范给你看”的这种理解,解释就在“示范”行为之中。“寻视着加以解释”也同理地道出解释的本质。而那个成为句子的回答,倒是蕴含在命题(Aussage)当中,而且是命题的存在论前提。
在专门命题中,“作为”并非才识出现,而是才始道出。
——第三十二节
在解释中所占有的领会有一个被称之为“先结构”的东西,它有三个结构要素——先行具有(Vorhabe)、先行视见(Vorsicht)和先行掌握(Vorgriff)。我在这里说它们是“结构要素”而不说“构成要素”是想强调:我认为此三者并非是单独的组成先结构的“部件”,更不是作为先结构的属性,而是解释所占有的领会被标识为一种先结构,这占有中可以从这三个结构要素中体现出来,可以说它们“同出而异名”。
这种解释一向奠基在一种先行具有[Vorhabe]之中。作为领会之占有,解释活动有所领会地向着已经被领会了的因缘整体性去存在。对被领会了的、但还隐绰未彰的东西的占有总是在这样一种眼光的领导下进行揭示的:这种眼光把解释被领会的东西使所应着眼的那样东西确定下来了。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视见[Vorsicht]之中,它瞄着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先行具有中摄取到的东西“开刀”。被领会的东西保持在先行具有中,并且“先见地”[vorsichtig]被瞄准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解释一向已经断然地或有所保留地决定好了对某种概念方式[Begrifflichkeit]表示赞同。解释奠基于一种先行掌握[Vorgriff]之中。
——第三十二节
先行具有的就是世界(Welt),前面说了,世内存在者是在世界中得到展示,即在一个因缘整体性中得到展示,世内存在者的存在都是互相勾连的,而非单独的“自在”。我们在谈论或使用“青蒿素”的时候,它是一种被用作治疗疟疾的中草药提取物,很显然此时它的意义已经和诸如“疟疾”、“中草药”和“青蒿”乃至更远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了,而它所勾连的这些世内存在者的存在又和更多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勾连在一起了,由此织成一张“因缘整体性之网”。我们在谈论或使用它的时候,并不会体现出它所勾连的这些存在,但它们确实是先行隐藏在前面了,“隐藏”是说它们不彰显,“在前面”是说它们是先有的,没有对它们的理解就没有对青蒿素的理解。这样的先行理解使得我们会将“青蒿素”作为一种如何如何的东西来解释,而不会作为另一种如何如何的东西(比如作为调味料)来解释,就如原文中形象地说是“切第一刀”,这便是先行视见。事实上,从原文的关于此两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前面所讲的“同出而异名”的意味了:先行具有是一种“有”,用传统的说法就是保持在“观念”中的有(当然我们要到最后摒弃诸如“人是观念”、“人是意识”之类的说法),其实践意义不明显,相反先行视见中有“视见”,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这个“见”理解为日常常说的“见”,而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看见”,其中蕴含了理解的意味——就像我们把西文语境中的“I see”也翻译为“我理解”,在中文语境中有时候也说“让我看看怎么回事”的“看”也不仅仅或者说本质上并不是真要去睁大眼睛看然后产生视觉。总之,“视见”和“开刀”这样的措辞,可以看出这里是具有实践意义的。不论只是“有”还是去“见”,都是解释对领会的占有的样式而根植于领会之中的,没有“有”就没法“见”,没有“见”那就根本不是解释,解释中的单纯的“有”是与实践哲学的宏旨相悖的。在解释之际,一些能作为被描述的东西(但没有真正地作为命题去描述)“上升”出来,那就是对有关世内存在者的概念的先行掌握。但并不是说是解释生出了概念的先行掌握,因为这种对概念的先行掌握仍然要基于领会,只是在解释之际它才浮现出来,它本来是“藏在下面”的而不是没有的。
在领会的筹划(Entwurf)中,存在者是在它的可能性中展开的。……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会性的栖身之所。……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及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
——第三十二节
可能性要“降落”于事实性当中,这个事实性就是可能性的筹划的方向。先结构引领着世内存在者以“作为……”结构展开,而如此展开的“原因”就是意义,所以意义始终是此在的意义,没有此在就是无意义。我们说繁衍是生物的本能,是生物存在的意义,而事实上是我们说“繁衍是生物的本能”,如果不是我们说,“生物的本能”根本上就没有,所以说依此去论证“人类的本能也是繁衍”是忽略了意义的本身的源头,是将那个展开存在的此在等同于了那些被展开的世内存在者。
话语(Rede)同现身(Befindlichkeit)、领会在生存论上同样源始。可理解性甚至在得到解释之前就已经是分成环节的。话语是可理解性的分环勾连(Altikulieren)。从而,话语已经是解释与命题的根据。可在解释中分环勾连的,更源始地可在话语中分环勾连。我们曾把这种可加以分环勾连的东西称作意义。……把话语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Sprache)。
——第三十四节
很明显,解释只是在展示意义,并非解释划分(Altikulieren,张汝伦译)理解,所以有在存在论上更原始的东西划分理解之所向的意义,它就是生存论上和领会同样原始的话语,不是日常的谈论中讲的那些语句,而是它们的基础,话语所划分的意义才能“进入”到个别的解释当中去展示。注意,领会之所向是意义,划分领会何所向的是话语。
我们现在把话语的分环勾连中分成环节的东西本身称作含义整体(Bedeutungsganze)。含义整体可以分解为种种含义;可分环勾连的东西得以分环勾连,就是含义。含义既来自可分环勾连的东西,所以它总具有意义。……言词吸取含义而生长,而非先有言词物,然后配上含义。……言词整体就成为世内存在者……。
——第三十四节
当我们在说出一个词语一个句子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这一个个语句的含义究竟在哪里?它来自话语对领会的划分,划分所得称之为含义整体。话语是“去划分它”的此在生存结构,所以我理解这个“含义整体”大概是个比较抽象的形式概念,含义整体再划分所得的含义便是可以通过言词道出的。“言词物”的说法已经很明显了,语句(言词)本质上被视为一种话语说出来的方式,所以说它是世内存在者,作为世内存在者的语句本身的自在是没有含义,是基于理解才有了含义,只不过一般不会有没有含义的语句,语句生而有含义。海德格尔后面的著作中还有“存在是语言的家”的说法。
这里要厘清“含义”与“意义”这两个概念。此两者在我们日常语言中用法也却有不同,似乎意义所表达的比含义更加“深远”,而事实上,依据我的理解,意义确实在存在论上比含义更加源始。意义是领会之所向,是“能在”到“是”的转化。意义其实就是领会本身,领会是存在之领会,所以其实意义就是存在,问“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在问什么是存在,这是在说存在论上的意义。领会(意义)经过话语的划分,才能进入到解释或语句之中进行展示,在解释中以“作为……”结构得到展示的“个别意义”才是我们日常用语中的意义。而含义无论在存在论上还是在日常用语中都是指那个作为存在者的语词的含义,它是由话语划分领会为含义整体后再划分得来的。
那么上面所言和存在论上的听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谈论听之前,我们需要先进一步描述话语本身的结构。话语的建构性要素有四:话语之所关(Woüber)、话语之所云(Geredete)、传达(Mitteilung)和道出自身(Sichaussprechen)。从此四者均体现出话语的说出性。
话语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话语。话语的“关于什么”(……über)并不一定具有进行规定的命题的专题性质,甚至通常不具有这种性质。……话语必然具有这一结构环节;因为话语共同规定着在世的展开状态,而它特有的这一结构已经由此在[在世]这一基本建构形成了。
——第三十四节
这个“关于某东西”其实就是话语划分领会之后的结果,让那个“天马行空”的可能性归于一种事实性并“落在”某物上,这个物可以是上手的世内存在者,也可以是语句。这种“落在”其实就是“在说出”,即说出性的体现。“关于什么”也不只是关于某世内存在者,还可以是关于我的目的,因为存在领会不只是关于世内存在者的存在领会,还是此在关于它自己的存在领会,这其中就包括了我的目的的领会。愿望、命令这样的东西都没有关于某个具体的世内存在者,却关于一种基于领会的我的目的。一个具体的愿望便是自我的(目的的)说出。事实上,我们日常对话中,首先且多半是关于你我的,而非关于一个世内存在者的描述性的命题,即使没有关于某个世内存在者现成性的揭示(所谓的客观描述),我们也可以谈关于它的感受(喜欢、厌恶等)。可见,这个“关于什么”结构中,此在的存在展示性就显现出来,不论是说出(关于)世内存在者还是此在自己,都是存在展示。
话语所谈的东西总是从某种角度、某种限度内说到的。任何话语中都有一个话语之所云本身,也就是在各种关于某某东西的愿望、发问、道出自身等等之中的那个所云本身。在这个所云中话语传达自身。
——第三十四节
这一结构在关于存在者的命题中尤其明显。当我们在日常中说“这杯水很热”时,它不仅仅是我把这杯水展开为“热的”,我们倒要接着问:“为什么这杯水被展开为‘热的’?”很明显我在日常中的这句话远非仅仅关于“这杯水”的客观的现实性的阐述,而是有更多的言下之意,比如提醒别人喝的时候要小心烫嘴。所以其实在这个命题中除了是在展开这杯水,同时还展开了我自己,在这个命题的为什么之中所“说出”的其实是我的领会。当话语划分领会而关于什么时,同样连带下来的就是源自于领会之中的“言下之意”。而在关于我的目的的语句中,话语之所关和话语之所云便几乎浑然一体了。
有所领会的共处的分环勾连是生存论原则上所领会的传达之中构成的。这种分环勾连“分享”着共同现身与共在(Mitsein)的领会。传达活动从来不是把某些体验(例如某些意见与愿望)从这一主体内部输送到那一主体内部这类事情。共在本质上已经在共同现身和共同领会中公开了。在话语中,共在以形诸言词的方式被分享着,也就是说,共在已经存在,只不过它原先没有作为被把捉被占有的共在而得到分享罢了。
——第三十四节
话语所划分的是此在的领会,而此在本质上又是共在,所以也是划分共同领会,划分之际所展示的也是共同领会。所以这里的传达更应该理解为分享,分享那个共同领会。话语的这一结构更加完善了此在本质为共在的图景,简单来说便是共在是话语可领会性和传达性的基础,如果不是共在,那么其实人们都是沉默不语的,说了千言万语却根本什么都没说,无异于对牛弹琴。没有共在,领会之划分便无法实现,更不谈它的说出性,领会始终“封闭”着。传统的主体论就有意识封闭于人的主体内的观点,而以共在为基础的话语便说明了这种主体论的片面性,此在就是这样划分领会并且展示(说出)的。此在向来共在,但却会隐而不彰,唯有话语划分领会后的传达之际,共在才被把捉占有,所以说共在又通过话语维持。关于共在详见第二十六节。
在话语之所云中得到传达的一切关于某某东西的话语同时又具有道出自身的性质。此在通过话语道出自身,并非因为此在首先是对着一个外部包裹起来的“内部”,而是因为此在作为在世的存在已经有所领会地在“外”了。
——第三十四节
这里讲的道出自身是指话语要进入它“现世的”存在方式,即表现为我们所听说读的语句,语句被说出时携带着含义,这含义就是来自于自身领会的,所以那些连携着的含义的说出就是存在之领会的展示,道出自身这一结构其实是话语说出性的最具象化的描述。但是道出自身不是从一个自我封闭的由内到外,在这里的那个“自身”最初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我的领会不封闭在我这里,而是要寓于世内存在者的,就算是在说某种关于我的感受,也是在共在领会当中的:我在说“我好困”之际,关于“困”的含义需是基于共同领会的。“我好困”确实是在说我的感受,但那是对我这个存在者的感受的描述。反对“封闭的自我”也是全书的主基调。
话语本身包含有一种生存论的可能性——听。……如果我们听得不“对”,我们就没懂,就没“领会”;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听对话语具有构成作用。语言上的发音奠基于话语;同样,声学上的收音奠基于听。此在作为共在对他人是敞开的,向某某东西听就是这种敞开之在。……此在听,因为它领会。……共在是在互相闻听中形成的。
——第三十四节
通过前文对话语的结构的描述,我们便得以正面描述存在论上的听的含义。简单来说,这个听就是在领会语言,它是话语的一种生存论的可能性,存在论上的听的结构其实就是话语的结构的变形:日常中我们听总是听他人说话并且能听懂,在听懂他人说话之际,领会已经先行划分了。作为听者的我,话语之所关同样也已经展开,所以我才能懂得所关者为何;随着领会划分而展开的话语之所关一同展开的话语之所云也已经在听者中展开,否则话语之所云才不会成为“言下之意”了;传达之中的话语的分享性已经说出了话语本身就不能只有“一个”此在参与,有听者必有说者,否则便没有话语可言,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说者是听者,听者也是说者,因为他们都在展开存在领会;同样的,道出自身就要有听者,没有听者自身便没有道出。这一切的核心便是话语的说出性,不说出就不是话语,既说出便是有听者,否则根本谈不上说出。
在这种意义上,就算没有声音也可以听,所以聋人也可以听,听力健全之人就算在纷乱嘈杂的菜市场也可以丝毫不听。所以蒋勋才说他在车水马龙喧嚣的街道上时却也感到像身处无人的荒漠中一样孤独。我在开头中说,生理上的听其实是被动的过程,只要是听力健全的意识清醒者,只要听力器官受到了声波的刺激,那便能产生听觉,然而当你不去听,那些产生的听觉却又有真正地“被听”吗?那些所产生的听觉又与我的存在有什么关系吗?
这种能听在生存论上是原初的;在这种能听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听到声音这回事。……听到声音也具有领会着听的存在方式。我们从不也用不“首先”听到一团响动,我们首先听到辚辚行车,听到摩托车。……要“听”到“纯响动”,先就需要非常复杂的技艺训练。……甚至在明确地听他人的话语之际,我们首先领会的也是所云;更确切地说,我们一开始就同这个他人一道寓于话语所及的存在者。并非反过来我们首先听到说出的声音。甚而至于说话得不清楚或说的是一种异种语言,我们首先听到的还是尚不领会的语词而非各式各样的音素。
——第三十四节
听其实也是一种领会,领会是此在的能在,所以这种听也可以说是“能听”。由此可见,生存论的听和日常意义的听确有明显区别,所以海德格尔将前者称为倾听(Horchen)。倾听是听觉的基础,就算听觉并未被主题化(像现代生理学一样),就算听觉本身并未以一种现成性展示出来,我们也可以听懂(听到什么),事实上我们在听时大多听见什么而非只是有纯粹的听觉。所以听到什么是“大多且首先”的,这个表述在本书中被广泛使用,特别是在讲世内存在者的上手性时3。首先是说生存论上的首先,即是一种在日常中除非我们“有意为之”,否则我们并不会不这样的现象,所以并不是因果链条上的首先,更不是时间上的首先。所以,并不是我们首先听到一段声音,然后我们的意识(大脑)为声音赋予意义,反倒是在听之际就已经是听到什么了,所听的是什么已经在那里(不是我这里)先行展开了。我们去倾听时,反倒很难听到纯响动,总是听到什么,在“有什么”之际,领会已经得到展示了。就算是我们去到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当地人与我们对话时就算我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我们也会认为他们是在“说什么”而非仅仅是在发出声音去刺激我们的听觉器官。
现代物理学和生理学已经把“声”和“听”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声是由物体振动所产生的,它可以借由特定的介质以波的形式进行传播。声波到达耳膜后继续沿耳蜗传导并刺激耳内听觉细胞产生膜内外的电位变化,即将声波转化为电信号,电信号沿听神经传播到达大脑后编译为听觉。声音到听觉的转化过程大抵如此,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所接受到的这个刺激——“听”的刺激难道不只是一种物理上的波吗?如果是,那这些声波的含义又是从何而来?如果不是造物者在创造这些声波之时已经为这每一段不同频率的声音都赋予了相应的意义,那么这不同的声音和我听到什么之间又有什么必然关系吗?这样的关系是通过什么逻辑或是什么科学方法论证或推导出来的吗?又或是人类基因之中固有的刻印吗?显然都不是。所以,这声音是什么首先是来自于我们的领会,在世界中与事物打交道而产生的对它们的存在领会,根本上是在世实践而来的,不是理性推导而来的,更不会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所得的结论。在前面论述世内存在者首先是作为上手事物而非现成事物和我们打交道时,大概也是这种路径,这也是在说所谓存在论上的“首先”。海德格尔所致力于的反传统存在论的核心也在于此——反对传统的认识论,认为我们是先有纯粹的感知然后给他赋予意义,这样往往会导致更多认识论上的难题出现,然而这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中这些难题根本不是问题,它们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这种认识论上的倒置导致的。我之前在刚读完斯通普夫的《西方哲学史》之后,我曾对别人说,文艺复兴之后到大概19世纪这段时间的哲学给我的感觉就是哲学家端坐在房间里,一直一直思考而得出来的。后面提到的这段时间哲学的在讨论存在问题上的问题时,大概就是展现出一个这样的“人的样子”。(详见第四十三节)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标题了。那么在听歌时,我们就不只是听一段段声音,而是所听的歌曲本身已经是作为什么而对我们展开,否则只是单纯的一段段声波,或者说乐器的振动何以触动心弦?
现身的“在之中”通过话语公布出来,这一公布的语言上的指标在于声调、抑扬、言谈的速度、“道说的方式”。把现身情态的生存论上的可能性加以传达,也就是说,把生存开展,本身可以成为“诗的”话语的目的。
——第三十四节
如果听不只是单纯的听觉,声在被听之际不只是单纯的声波,那么歌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词加曲。歌在被听之际,词曲已经是浑然一体而不可拆分的了,因为歌者所唱之歌词的音调、抑扬、速度等皆是在话语之中展示的。如果说说语词和操劳中的解释都是领会之展示的形式,那么这些音调、抑扬、速度都可以是领会展示的形式,通过它们能说出仅仅是语句的含义无法展示的东西,原文中就提到了现身情态,现身情态的在“现世”中便表现为我们喜怒哀乐的情绪,所以通俗而言,歌者的演唱方式传达着他自己乃至歌词曲创作者的感情,这一点在生存论上是有所基础的。
在这一点上诗也是相同的。我看过叶嘉莹做主持的一个赏古诗词的系列节目,她在朗诵诗词时并不只是诵读,而是直接有所音调地“唱”出来,我想她是想最竭力地还原作者当时最本真的情感。
——《神曲·地狱篇》[意大利]但丁 著;田德望 译Cred’ ïo ch’ ei credette ch’ io credesse.
现在我认为当时他是认为我认为。
这一句的前文大概是但丁在地狱的第七层第二环中听到哭的声音却不见哭的人,他由此陷入了迷惘而止步不前。这一句异常矫揉造作,利奥·史皮策(Leo Spitzer)认为,这里表现出但丁遵照维吉尔的话注意去看稀奇的事物,但只听到哭声时,不觉陷入迷惘当中,和维吉尔的思想交流一下子中断的情况;这行拙笨的、结结巴巴的诗句是但丁精神上这种隔阂和混乱状态的拟声法的写照(versione onomatopeica)。我们常说诗词有不可译性,大致就是这种感觉,可以看到原文中连用多个“c”音来表达这种混乱结巴、磕磕绊绊的感觉,而在译文中却几乎看不到。译文只是单纯的语句含义的转换,而在语句的含义之外所表达的便隐而不彰了。同样将中国的五言绝句译为西文诗也是风味尽失,其中的平仄声调和和谐韵律很难传达转化。这些在诗中语句含义之外所说出的,我愿称之为“言外之意”。
Raphèl mai amècche zabì almi.
——《神曲·地狱篇》[意大利]但丁 著
这是巨人宁录所说的话,他是巴比伦的第一代国王,传说是他计划建造巴比伦塔。根据《旧约·创世纪》中说,那个时候天下人有同样的语言,他们来到示拿地的平原上后,就动工建造一座通天塔。耶和华说他们有一样的言语,如今又计划建一座通天塔,那他们便没有什么事干不成了。于是他就扰乱了人们的口音,语言便彼此不通了,结果他们被迫停工,分散开来。——若是单看这则故事,耶和华扰乱人们的口音而使语言不通,仿佛是在说在语言之前的话语是此在在世存在所共有的,是否隐约展示出了“话语-语言”结构?——《神曲》中的这句话本身就没有任何含义,注释家本维努托说,“这些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在这里只是用来表明他的语言任何人都不懂得,因为他的狂妄结果使世上的语言分为许多种。这就是作者的命意……”可见,语句甚至不需要含义也可以传达某些意思,此中之意便可以通过语音语调等传达。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说,诗比历史更科学、更严格,因为诗给我们普遍真理,而历史给我们特殊事实。诗作为一种语言是“完整的”在传达领会,相比之下历史只是“部分的”陈述事实。
诗与歌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汉语的日常用语中都有“诗歌”一词而将此两者合称1,日语中“诗(うた)”和“歌(うた)”读法相同,虽然我没做过语言学研究,但我猜想是人们都发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它们都兼具“言外之意”2。所以歌中之词曲在听之际便是不可分的,因为“曲”是“歌”这一完整的语言的一部分,没有歌中的曲词二者缺一在传达上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这样的传达就是容易出现偏差的传达,当然我并非因为纯音乐传达的不完整而拒斥其艺术性,相反,不完整的传达本身或许就是一种艺术性的体现,即所谓“朦胧美”。
长注释
1.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喜欢玩拆解德文词的游戏,运用其词根来对一些日常德文词进行他的存在论阐释。比如Entwurf在日常德语中指“计划”、“草稿”、“草图”等意思,但海德格尔将这个词视为“Ent-wurf”取“ent-”的“分开、离开”含义,取“wurf”源自于“werfen”的“投掷、投射”含义,从而让这个日常词语形成了生存论-存在论的意义关联。第二版中译本译为“筹划”,张汝伦译为“投开”。中文语词有不同于西文语词的特殊性,是否有学者针对中文语词进行类似于这样的解构,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新视角新结论?(添加于2024.10.20)
2.日语中常有多汉字同读音,而每个汉字本身又有其独特意义,寻找更多这种不同汉字在日语中读音上的相同是否提供了关于某些汉语语词的更源始的意义的信息?(添加于2024.10.20)
3.实际上在第三十四节前面,海德格尔使用了“语词物”一词,说明语词(语句)在日常中也作为上手事物被我们“使用”。这一点作为象形文字的中文应比西文更显著,相信我们大都有过当同一个字在一段话中多次出现而被我们看到时,那个字仿佛变得“陌生”了。这个陌生并不是我们遗忘了它的含义,反倒是我们在阅读一段话时,其实并没有先阅读每一个字词,再给每个字词以含义,然后继而理解由多个字词所组成的一段话的含义,最后以此类推地理解整篇文字。而是我们早已领会了每一个语词的含义,以至于当我们在阅读时根本没有留意某个字词的本身的“形态”——这方面它就是陌生的。(添加于2024.1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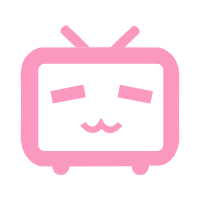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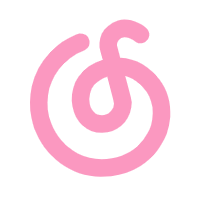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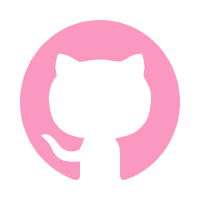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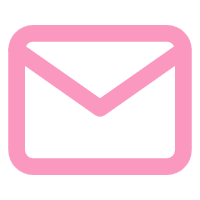


Comments NOTHING